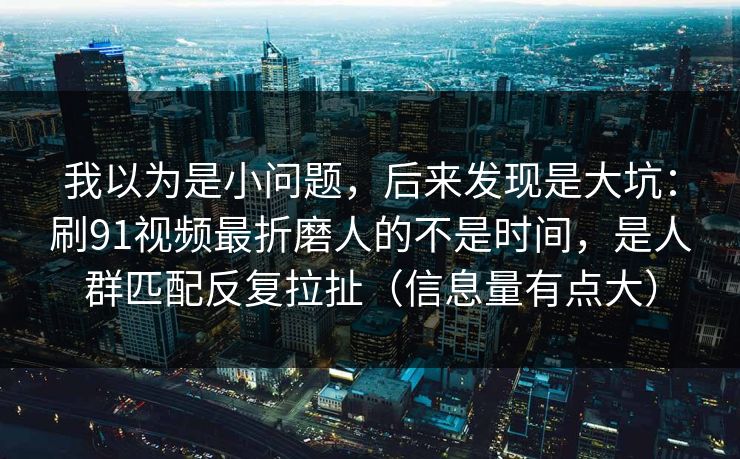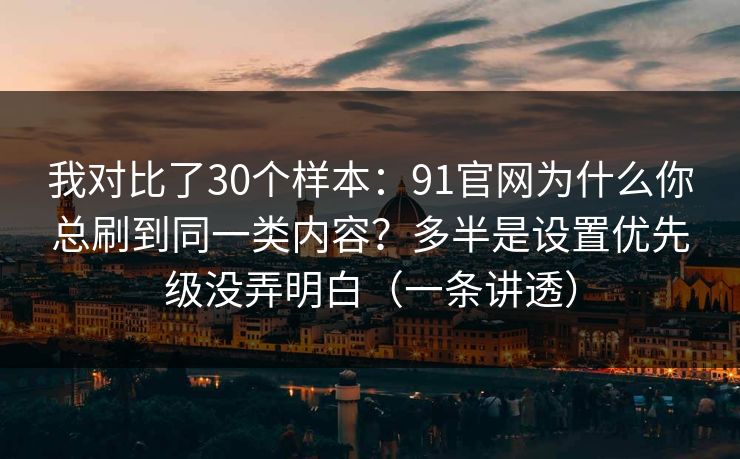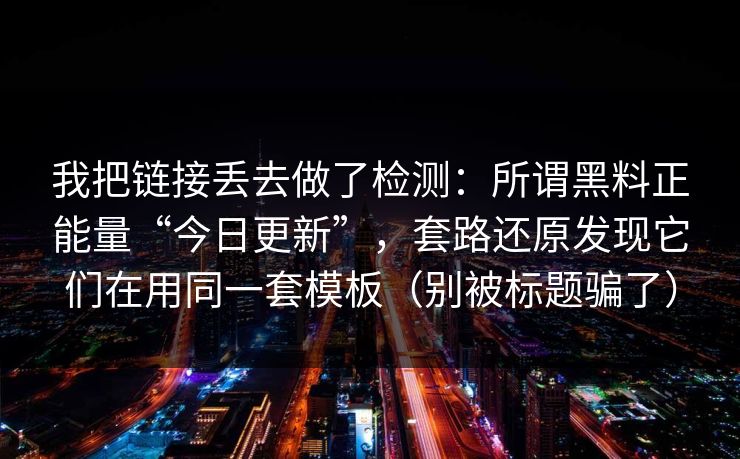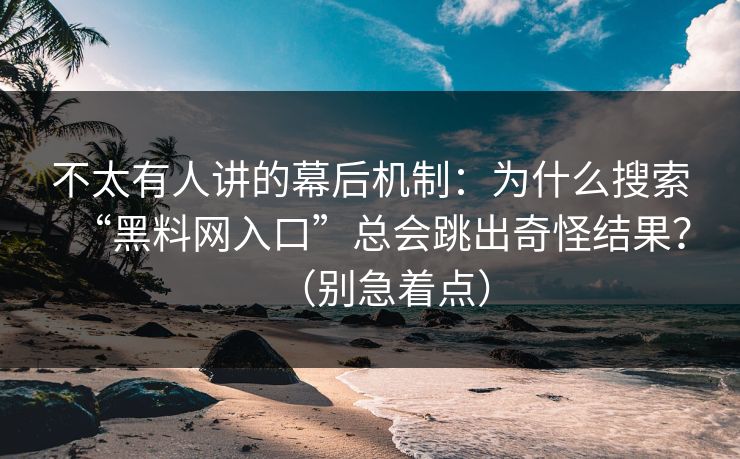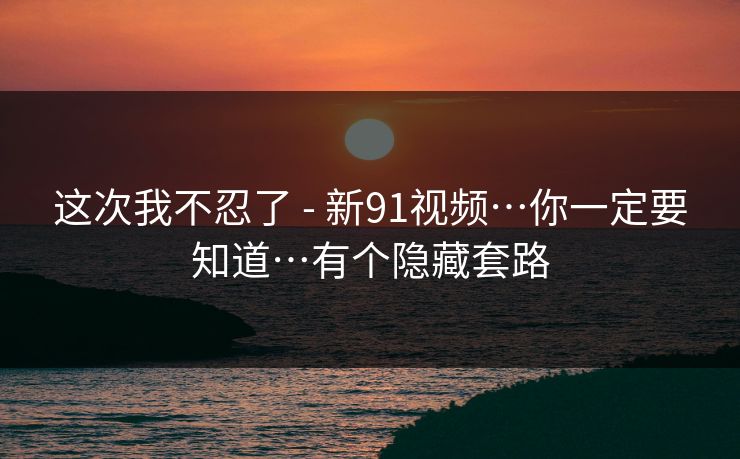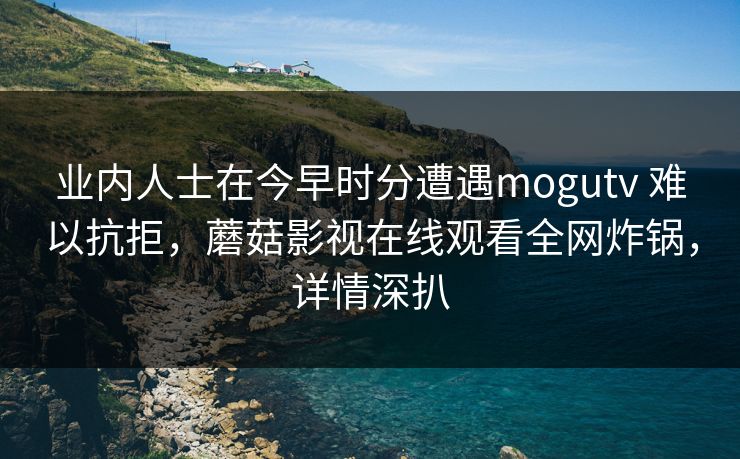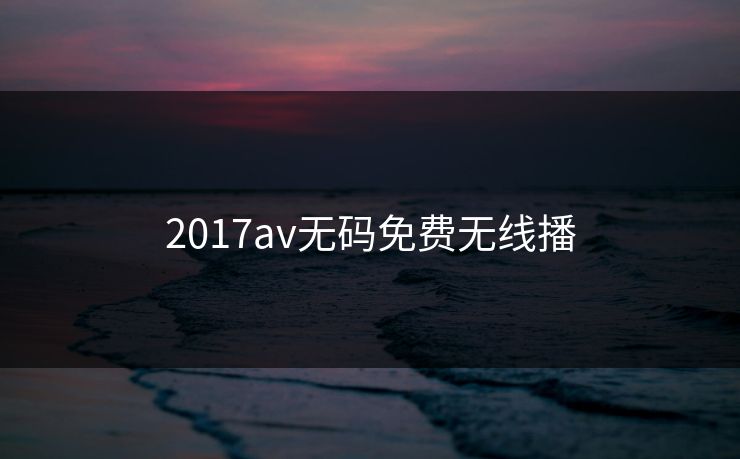初雪迎春,双生如约而至
北方的腊月总是凛冽的,寒风卷着细碎的雪花,敲打着窗棂。这是我搬来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冬天,也是我第一次独自在外过年。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冷清而孤单的春节,却因为一对双胞胎姐妹的到来,变得截然不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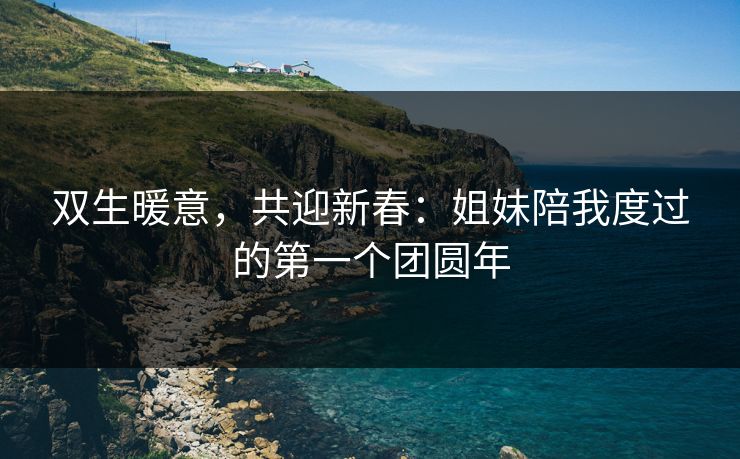
她们是我的大学同学,小雅和小悦。名字如人,一个文静温和,一个活泼开朗,虽是双生,性格却像冬日里两种不同的光——一是暖阳,一是星光。得知我今年不回家,她们二话不说,买了车票来到我租住的小公寓。“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过年?”小悦眨着眼睛,语气不容拒绝。
小雅则默默递过来一盒家里捎来的年糕,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。
除夕前一天,我们一起去逛年货市场。人潮涌动,红灯笼、春联、糖果和炒货的香气混杂在一起,年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小悦兴致勃勃地挑着窗花,小雅则细心地比较着各类干果的价格。“这个好看,贴你窗户上!”小悦举着一对胖娃娃抱鲤鱼的剪纸,眼睛亮亮的。小雅轻轻摇头,“还是选对称的福字吧,寓意好,也适合你房间的布局。
”她们你一言我一语,一个感性一个理性,却默契地为我打点好了一切。
年夜饭是重头戏。我们决定自己动手,在我的小厨房里折腾出一桌菜来。小悦自告奋勇负责炖肉,结果手忙脚乱差点烧糊了锅;小雅无奈地接过勺子,一边补救一边耐心地教她控制火候。我负责洗菜切菜,听着她们拌嘴又协作,忍不住笑了起来。那一刻,锅里的热气、窗外的雪光和她们的笑声交融在一起,狭小的厨房仿佛被某种温暖的结界笼罩。
饭菜上桌时,已是华灯初上。我们以茶代酒,碰杯祝福。小雅细心,给我多夹了几块鱼,“年年有余”;小悦调皮,抢着吃了饺子里的硬币,“嘿嘿,明年运气是我的!”电视里春晚的歌声隐约传来,我们却更专注于彼此眼中的光彩。第一次,我不再觉得这个城市陌生。双胞胎姐妹像两颗扎根在此的树,让我仿佛也有了归属。
夜深时,雪下得更大了。我们挤在沙发上盖着同一条毯子,聊起大学时的糗事、未来的梦想,还有那些回不去的家乡年味。小悦突然说:“以后每年,只要你需要,我们都来陪你过年。”小雅轻轻点头,没有说话,却握住了我的手。掌心传来的温度,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。
晨光辞旧,默契常伴新岁
大年初一的清晨,是被小悦的惊呼声唤醒的。“下雪啦!好厚!”她趴在窗前,像个孩子一样雀跃。小雅已经悄悄起床,煮了一锅红枣桂圆茶,香气弥漫在整个房间。我们裹上厚厚的羽绒服,决定出门踏雪迎新。
街道上行人稀少,雪地洁白平整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重置了一般。小悦团起雪球偷袭小雅,小雅敏捷地躲开,反而把我推到前面当“盾牌”。一场即兴的雪仗就这样开始,笑声惊起了路边树上歇息的麻雀。那一刻,年龄、烦恼仿佛都被甩在了身后,我们只是三个在雪地里嬉闹的挚友,也是彼此选择的家人。
午后,阳光钻出云层,雪地反射出细碎的金光。我们决定去附近的庙会逛逛。舞狮、糖画、吹糖人……传统年俗热闹非凡。小悦对一切充满好奇,拉着我们逐个摊位体验;小雅则用手机认真记录每一个瞬间,“这些以后都是回忆。”她说着,帮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围巾。
在一个手工编织摊前,我们停了下来。摊主是位慈祥的老奶奶,教我们用红绳编平安结。小悦学得最快,手指翻飞很快完成一个;小雅编得慢些,却更精致结实;而我总是打错步骤,屡屡失败。她们没有丝毫不耐烦,一左一右地指导我,一个说步骤,一个纠正手法。最终,三个略显稚拙却充满心意平安结诞生了。
我们互相交换,约定要一直带在身边。
夜幕降临,庙会的灯笼逐一亮起。我们坐在长廊下分享一袋刚炒热的栗子,看着人来人往,享受这片刻宁静。小悦忽然说:“其实过年不在于在哪里,而在于和谁一起。”小雅接话:“嗯,有真心相伴,哪里都是家。”我望着她们被灯笼映红的侧脸,心里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感激。
这座城市、这个新年,因为她们,从孤单的驿站变成了温暖的港湾。
分别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。送她们去车站时,雪又开始飘落。小悦塞给我一大包家里寄来的特产,叽叽喳喳地嘱咐要怎么吃;小雅则悄悄在我背包侧袋放了一个信封,后来我发现里面是一张手绘的贺卡和她们姐妹的合影,背面写着:“新年快乐,永远姐妹。”
列车缓缓开动,她们在窗口挥手,笑容灿烂如初春的晴空。我站在月台上,直到列车消失在视线尽头。雪花落在脸颊,凉意中却带着暖。这个年,或许没有鞭炮齐鸣的喧嚣,没有大家族围坐的热闹,但它有我从未体验过的细腻与深情。双胞胎姐妹用她们的默契与温暖,为我编织了人生中第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春节记忆。